文 子 :古 居 秋 声
古 居 秋 声
□ 文 子
文韵天水,古迹颇多,胡氏古民居就是其中最有韵味的。
秋意是在不经意间漫上藉河两岸的。中秋才过了几日,风里那点温存便散尽了,换作清透的凉。至天水古城民主西路,两株古槐默然伫立,盛夏时泼天盖地的浓荫,此刻已褪成疏疏朗朗的几笔水墨,枝干在青空里瘦硬地岔开,像是老天爷不经意间留下的笔痕。目光落处,是那两扇胡氏古民居的黑漆大门,秋阳斜斜地照着,门楣上“副宪第”的匾额幽然沉静,不像木头,倒像一块凝滞了的时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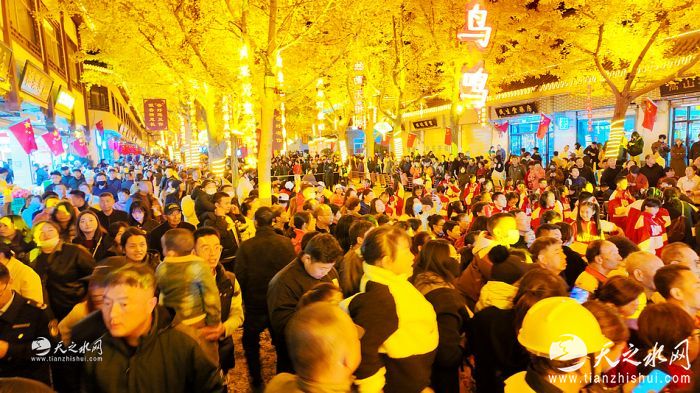
进古居门的刹那,秋风微起,拂过颈项,凉意便倏地钻了进来。院里已寻不着桂花的香,想是早被这几场秋雨收拾尽了。只有石阶旁倚着几丛秋菊,花瓣是那种蜷着的、怯怯的淡紫,在清冷的光里吐着些许孤高的艳。正厅檐下的彩绘,到底禁不住经年风雨的磋磨,牡丹失了鲜妍,仙鹤的羽翼也模糊了,昔日金碧辉煌的过往,都化作梁间一缕若有若无的烟霞。正凝神间,穿堂风过,廊下悬着的铁马叮咚作响,那声音不似夏日的沉闷,像是碎玉敲着冰,清凌凌的,一声声,仿佛不是在风中,而是在时光流溪里的叩问。
胡氏古居,是静默的。那静里,有往昔的热闹。移步书房院,但见几竿紫竹染了薄霜,叶缘泛着些微的枯黄。藏书阁的木窗半掩着,秋阳从隙缝里漏进去,光柱中无数微尘缓缓浮沉,恍若无数微小的生命在无声地舞蹈。恍惚间,似有极轻极细的翻书声窸窣传来,是胡氏子弟悬梁刺股的余音么?还是秋风这不知趣的客人,在翻动无人问津的残页?抬头望,门额上“棫朴英材”四个字,在秋光里显得格外沉郁。一个家族对文脉的坚守,那弦歌不绝的盛景,到如今,也只凝成这匾额上一行风干的墨迹了。
不觉间已走到绣楼之下。雕花的木栏积了薄薄一层尘,那“梅兰竹菊”的透雕,在斜光里将影子投在斑驳的地面上,纤巧得叫人心疼。这精致的牢笼里,曾锁着多少如花的青春?那些素未谋面的女子,是否也曾透过这花格的空隙,偷偷窥探过墙外那一方窄窄的、却属于自由的天?台阶上的苔痕湿滑滑的,想是秋雨初歇未久。不知多少个月明之夜,有窈窕的身影曾倚在这冰冷的栏杆上,看那天上的月,圆了又缺,缺了又圆。中秋刚过,月还丰腴着,留着圆满的余韵,可这人间的庭院里,别离却早已是常态了。
戏台已空。凌霄院的藤蔓失了夏日的精神,牵拉着,只有几片倔强的叶子还攀在墙头,守着这最后的一线秋光。倒是北宅子院里那株老槐,最是知情知性,正毫不吝惜地飘洒着金黄的落叶。那叶片悠悠地旋舞着,不情愿似的,一片,又一片,铺满了青石地面,踩上去,便发出一种细碎的、如同叹息的声响。太常第的厅楼在落叶后默然矗立,硬山式的屋顶划出利落的线条,像用尺子比着,将一方碧空分割得整整齐齐。这里,曾是胡忻秉烛夜读、挥毫泼墨的地方。那《请发内币赈荒疏》上的墨迹,早已干结了四百年,可纸页间透出的那份为民请命“北海瑞”的风骨,却似这屋宇的梁柱,任岁月侵蚀,兀自挺立不朽。
移步至后院,目光便被那“一坡水”式的厢房引了去。青瓦斜斜地铺开,檐角如飞鸟展翼,与京畿四合院的雍容大不相同,自有一番陇上人家的简朴与因地制宜。庭院的四面,廊庑环通,想来即便秋雨连绵的日子,也可沿着这廊子,从容地穿行于各个院落之间,衣衫不湿。这构造里,有着北方的硬气与江南的柔美,藏着的是古人“风雨无阻”的处世智慧,更隐喻着一个大家族血脉相连、息息相关的温存。
民俗博物馆里,一件陈列的绣裙吸引了目光。裙上金线绣出的龙凤,在透过窗棂的秋光里,显得异样沉静。那曾经灼灼耀眼的五彩,已被岁月这只无形的手,洗练成温和的、近乎苍老的色调,像一个年华老去的贵妇,依然保持着优雅的、从容的手势。正出神间,窗外天井里忽地掠过一声雁鸣,清厉而急促。抬头望去,一队雁阵正掠过高檐划出的一方蓝天,匆匆南去。它们年复一年地经过,可还记得,这四百年来,从同一片天空下,看过这庭院里多少次月缺月圆,时光变迁……
不知不觉间,秋风穿过空寂的廊庑,带着木叶清苦的香气,拂在脸上,已是十足的凉意了。胡氏古居在渐浓的晚照里,静默得像一个入了定的老僧,唯有青瓦缝里几茎秋草,在风里轻轻地摇曳,像是它无声的呼吸。那些数不尽的荣辱兴衰、悲欢离合,到如今,都化作了檐角下几串古旧的风铃,在这渐凉渐浓的暮色空气里,敲击出一串串清越的、泠泠然的秋声。
此刻,天地俱寂,唯闻此声。这胡氏古居的秋日,不正是天地与人文交织成的一幅纯净长卷么?它让每一片青瓦,每一缕风,都成了历史的见证者与述说者。站在这庭院中央,仿佛能听见时间流过的声音——它不是消逝,而是沉淀,将所有的浮华都洗去,只留下这如水的平静,如秋声般清朗的风骨。
【作者简介】:文子,甘肃山丹人,天之水网专栏作者。曾在《甘肃日报》、《甘肃文学》、《张掖日报》、《张掖作家》、《张掖网络作家》、《作家联盟》、《天之水网》、《焉支山》等报刊、网络平台发表数篇作品。